【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揭示了知识发展战略的内涵,认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知识发展战略”,实现了发展战略的重大进步。接着,文章提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分析框架,据此分析了中国的真实国情,指出中国长远未来的发展必须有效解决“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问题。文章进而指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背后是显著的知识水平的地区差距,知识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政府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知识发展战略是中国在长远未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的优先战略选择。文章最后提出了以基本知识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知识发展战略构想。
一、知识发展战略:21世纪新的发展战略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使人们不断加深对发展的认识,从而推动发展战略的演进,而演进了的发展战略又进一步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发展的关键。因为,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在20世纪末,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进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战略——知识发展战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这种新的经济增长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我们称之为“知识发展战略”。之所以说这是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进步,不仅在于这种发展战略第一次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发展手段,更在于它直接把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注:阿玛蒂亚·森提出,“发展就是拓展人类自由(Human Freedom)的进程”,“在这种观点下,扩大自由被视为个人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实际的自由包括能够免于饥饿、营养不良、避免疾病以及夭折等威胁的基本能力,以及识字、识数、享受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自由权利”。显然,“扩展自由”主要是提高人的基本能力,在21世纪,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知识能力。而知识发展战略正是着眼于发展人的知识能力,从而提高人获取自由的能力,因此,我们说知识发展战略实现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参见Ama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Rardom House,Inc., 1999。),从而将极大地促进人本身的发展,即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事实上,知识发展战略的两个基本要素——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不是20世纪末的新事物。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过对传统发展战略的反思(注: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大部分国民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旧。于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起来呼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例如,达德里·西尔斯提出了发展的基本含义:“对一个国家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作‘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参见达德里·西尔斯《发展的含义》,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论文,新德里,1969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增长仅仅是物质量的增长,发展应当包括一系列社会目标(注:例如,迈克尔·托达罗总结道,所有社会的发展至少必须具备下述三个目标:增加能够得到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提高生活水平,即不断增加物质上的福利,而且还能给个人与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扩大个人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参见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黄卫平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六版)。)。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各种替代发展战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发展战略”。它的出现标志着发展观的转变,即把发展的根本内涵从“经济增长第一”转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道德价值方面。随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进一步形成,它指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个民族的价值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更是制定了一套全面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注:UNDP在1990 年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它的人民。发展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使人民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成为可能。基于这种理念,UNDP编制了包含出生时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各级教育毛入学率和人均GDP等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参见UNDP各年《人类发展报告》。)。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理论早就指出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就得到了很精辟的论证。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技术对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认识,即技术进步是抵消收益递减的主要力量。而且,经济学家还不断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还有间接的影响,以至于经济学家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全部经济增长,即使是因资本积累直接引起的增长,最终都可以被归因于技术进步”(注:参见理查德·R·尼尔森、保罗·M·罗默《科学、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载于戴尔·尼夫等主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邸东辉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进一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新增长理论学家则通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了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是,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前,知识终究只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增长手段。直到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迅猛发展,并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才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真正由一种思想变为实践。
因此,从根本上讲,在20世纪末以前,人们执行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战略,经历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虽然,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被独立地提了出来,但是,二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虽然已经认识到发展的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持;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已经认识到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观层面上还是陈旧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论”,因而也不能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
1998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知识促进发展》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成型。知识发展战略比1996年开始兴起的知识经济有更广泛的含义。在这里,知识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而且还成为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因素——知识驱动财富创造,知识促进人类发展,亦即知识同完整意义上的发展从理论上联系起来。
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也不仅仅是发展高技术或者信息与通信技术,而是要求政策、制度、技术、人员和政府之间有效互动,促进知识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有效应用。可以说,知识发展战略不是简单的帮助IT精英制造数字神话的战略,更重要的是“使母亲、农民、工人、企业和政府获得知识,从而改善生活的战略”(注:Carl J.Dahlman, Jean-EricAubert, China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Seizing the 21"Century.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D.C.,2001.)。 这一战略在以知识差距解释发展差距的基础之上,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缩小知识差距,以知识促进发展,进而缩小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
知识发展战略继承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的传统,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日益扩大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s)问题,即不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内部知识分布的不平衡性,指出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资本差距,还表现出创造、获取、交流和利用知识能力上的差距,而且这一能力的不平等甚至远大于收入上的不平等。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知识发展战略正是着眼于缩小差距,以达到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目的。这就使得知识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知识发展战略与中国的长远未来
(一)中国的真实国情:“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与“一个中国,四种社会”
发展战略的新发展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情况。什么是中国的真实国情呢?我们把它概括为两个基本特点,即“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
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真实国情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参照世界银行对世界各收入组的划分, 根据购买力平价(PPP )计算的人均GDP水平,我们把中国人口划分为四类收入组, 即属于“四个世界”(注:根据分析单元的不同,对于四个世界的划分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划分,根据家庭的人均收入将其分别归为四个世界。但是,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政策意义,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划分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一种方法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划分。这就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之内的人口在收入上是均质的,显然这个假定离现实有较大的差距,事实上,一个省(市、自治区)往往也会有四个世界同时并存。但是,考虑到我们是从全国的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省(市、自治区)是国家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并且省(市、自治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发展战略的主要决策者,因此这个划分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第二种方法由孟健军博士提出,按照沿海和内地、农村和城市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即沿海城市为第一世界,内地城市为第二世界,沿海农村为第三世界,内地农村为第四世界。此外,严格地讲,世界银行确定世界各国的收入类型依据的是国民收入GNI(即GNP),但是统计资料中缺乏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NI数据,这里使用各地区的GDP值参与国际比较。我们的统计中,没有包括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数据资料。)。2000年,第一组人均GDP(PPP)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9210美元,PPP),我们称之为“第一世界”,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省份的发达城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5%左右。其中,深圳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22304美元,远远超过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第二组人均GDP(PPP)介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600美元,PPP)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之间,为“第二世界”,包括东部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中部的黑龙江的发达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一些大中城市的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第三组收入高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80美元,PPP), 但低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第三世界”,包括东部的河北、海南以及中西部的发达地区,估计人口在3.3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四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及边远地区。这些地区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必须指出的是,严格的四个世界的划分边界并不能同省(市、区)的边界重合,因为各个省(市、区)之内也有显著的人均收入差距。我们在这里是根据各省的人均水平,将中国各个省(市、区)分为四组,大致描述各个地区作为整体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见表1)。
总之,从人均收入上看,中国是四个世界并存,但是不发达世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是主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4。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还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相应地,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中国的真实国情是“一个中国,四种社会”。从总体上看,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大量的劳动力还分布在农业领域。与此同时,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虽然还不发达,但是都有一定的发展,并且在局部地区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四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同时并存:一是农业经济,其就业比重将近50%,这相当于美国、法国和德国1870年的水平(见表2);二是工业经济(包括建筑业), 劳动力占23%;三是服务经济,就业比重为22%;四是知识经济(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等),其就业比重占5%。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正三角形社会,即中低收入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和传统工业、服务业就业占大多数。我们正是在这一国情条件下,在多个世界并存、多种社会并存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知识化的。这决定了: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不断的量变进而质变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条件下,我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逐步完成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时间所完成的业绩。具体来讲,在21世纪我们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从不发达到中等发达进而到比较发达,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进而到较高收入;二是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形态走向现代社会形态,实现经济转型,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工业和服务经济进而到知识经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两大问题决定了中国长远未来发展的前景。
表1 中国各地区人均收入及排序分布(2000年,美元,PPP)
附图
注:1.这里的“中国”指不包括港澳台的中国大陆地区,下同。
2.第一个括号中为人均GDP值,第二个括号中为在世界207个国家中的排位;中国人均GDP为3976美元(PPP),在世界207 个国家中列122位。
3.PPP表示“购买力平价”,按照世界银行(2002)数据计算(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CD-ROM, 2002)。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摘要》和《2002年世界发展指数》数据计算。
(二)知识差距:分析中国发展差距的综合框架
我们发现,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知识差距。为了对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知识能力差距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建立了中国各地区综合知识能力评价框架,并计算了中国各地区综合知识能力指数(见表3 )(注:衡量一个地区知识发展状况的指标包括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三个方面,分别采用百万人口国际论文收录(包括SCI、EI、ISTP三种检索工具收录)数、百万人口专利批准数、人均外国直接投资(FDI)、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入学率、万人口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以及人均订阅报纸数、电话普及率和万人口电脑数来衡量。以全国平均水平为100%,将这些指标指数化,加权平均可得各地区知识能力指数。参见胡鞍钢、熊义志《中国各地区知识发展差距:特点、成因及对策》,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从综合知识能力指数上看, 我国知识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综合知识能力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知识能力处于高水平和中上水平的地区全部在东部;中西部除吉林、湖北、黑龙江和陕西综合知识能力为中下水平之外,其余省份全部为低水平地区。
表2 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国际比较(1820—1998年,%)
附图
注:NA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1820—1992年数据引自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6年;1998年数据根据《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表8—3计算。
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知识发展差距的同时,各区域内部知识发展也极不平衡,一些省市区由于综合知识发展水平或者某一项知识能力远高于周围地区成为知识发展的中心,使得全国的知识发展水平的分布在总体上出现东高西低的同时,又形成若干高水平的知识发展中心。北京、上海为全国的知识生产中心,而广东为东部的知识生产中心,吉林(长春)、湖北(武汉)和安徽(合肥)为中部的知识生产中心,陕西(西安)、四川(成都)和甘肃(兰州)为西部的知识生产中心。
既然中国各地区之间同时存在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和知识能力差距,那么,知识能力差距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涉及如何解释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从早期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古典经济理论,再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数百年来,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这里要提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罗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结为技术进步。这里,索罗提出的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是指“总量生产函数的变化”,因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指经济增长中人均资本所不能解释的部分,所以又称为“索罗余项”,其中所包含的因素和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分析(注:R. 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XXXIX, August, 1957, pp.312-320.)。在这一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因素。针对这一问题,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来自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以生产中积累的投资代表知识的积累,从而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代表人物有P.罗默(注:P.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vol. 94, 1986, pp. 1002-1037. P. Romer, Growth Based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vol. 77, 1987, pp. 56-62.)、巴罗(注:R. Barro,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1991, pp. 407-443.);第二类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对R&D活动的资源投入,被称之为人力资本模型,代表人物有卢卡斯(注:R. E. Lucas, On the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Economics, vol. 22, 1988, pp. 3-42.)、罗默(注:P.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1990, pp. S71-S102.);第三类则是分工演进模型,以杨小凯和博兰德(注:Yang, Xiaokai and Jeff Borland, A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1991, pp. 460-482.)为代表,从专业化和分工的演化研究解释经济增长。
表3 各地区综合知识能力差距:知识发展指数(KDI)排名(1998年)
附图
注:全国KDI=100%。
资料来源:胡鞍钢、熊义志:《中国各地区知识发展差距:特点、成因及对策》。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解释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综合的框架。在这个综合的解释框架中,许多因素本身(如地理因素)是不能改变的,而且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会由于技术变迁而发生改变(注:Jeffery Sachs和林毅夫曾就这一话题展开过有意思的讨论。Sachs认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指出内陆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比较穷。林毅夫举出了历史上的反例:十二、三世纪的蒙古帝国就是内陆国家。Schas 认为这正好是技术变迁带来地理上的比较优势改变的实例,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蒙古的地理位置正好使之在养马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能成为当时的帝国。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亚欧大陆之间的陆上通道被海上通道所取代,蒙古帝国就不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了。参见Jeffery Sachs 《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演讲》,2001年5月26日。引自http://ccer. pku. edu.cn/newsletter/2001/251.htm。),相比而言,技术、教育、信息等因素则是更为活跃的因素,特别是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值得指出的是,其作用机制已经得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综合知识能力正是包含技术、教育和信息等因素在内的一个解释经济增长的综合框架。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在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分析中发现,物质资本只能解释这些差异中不到30%的部分,其余的70%以上要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构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无形因素,即知识因素和制度因素。我们曾通过对1978—1995年期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其他不可解释因素占8%(注:参见胡鞍钢、熊义志《中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及对策》,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从综合知识能力指数与人均GDP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 二者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综合知识能力指数越高,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相比之下, 矿产资源则表现出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见图1)。人均GDP处于高水平的地区全部为人均矿产资源低水平或极低水平的地区,而人均矿产资源处于高水平地区的人均GDP 全部为低水平。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路径依赖”。一般而言,矿产匮乏的省份更多依赖于开发利用其丰富的知识资源,同时开放程度高,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能力强;而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则更多地依赖于开发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开放程度低,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贸易的能力低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丰富是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但在市场需求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之下,矿产资源丰富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注:林毅夫称这种现象为“丰富自然资源的陷阱”。因为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处于劣势:一是丰富的人均自然资源带来工资率的上升,引起资本的转移;二是由于政府可以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弥补扭曲性政策带来的无效率,使得政府采取扭曲性发展策略的可能性加大。)。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现象的背后是各个地区之间显著的知识差距。知识是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重要的可控因素。中国能否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两大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解决知识差距的问题。
附图
图1. 知识以及自然资源与人均GDP关系的散点图
注:图中每个数据点代表中国大陆一个省(市、区);PPP 表示“购买力平价”,按照世界银行(2002)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人均GDP数据来源同表1;知识指数来源于前揭胡鞍钢、熊义志2000年论文;人均自然资源潜在价值指数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三)知识发展战略:中国长远未来发展的优先战略选择
中国发展的长远未来就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即消除“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现象,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不断增强人民发展的能力,使人民长寿、健康和有创造性地生活,避免出现边缘化的现象。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这一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克服制约中国发展的资源瓶颈,开发和利用中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形成最大的发展资本。这就决定了中国要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统一到以人为中心上来,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必须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改变中国当前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状况,就要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全面发展战略。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着眼未来,考虑可持续发展,协调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知识发展战略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条件之下,最重要的发展能力是人民的知识能力,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民的知识资产,最大的发展中危险是“知识隔离”,与现代化无缘。知识发展战略就是要发展人民的知识能力,增加其知识资产,保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内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知识发展战略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知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知识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知识发展战略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知识发展战略是推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培育中国长远发展能力的战略,它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消除瓶颈或者提供起飞的动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因此,知识发展战略是中国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并且还应当成为优先的战略选择。这不仅出自理论的推导,还基于历史事实。世界上国家之间成功的经济追赶的例子证明,后发国家对先行国的追赶具有知识因素先行的特征。世界现代化进程当中,曾经先后发生三次成功的追赶: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大约43年时间赶超英国;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如果以追赶国人均GDP相当于先行国人均GDP的比例来衡量经济追赶的进程,以追赶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初等教育当量年,即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年数分别以2和1.4为权重,折算为初等教育年)相当于先行国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追赶的进程,分析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可以发现:它们一般具有教育追赶先行模式(见图2)。图中对角线左上方表示教育追赶先于经济追赶。此外,我们在对地方干部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中西部的县处级干部对于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也有较高程度的认识,超过60%的被调查者认为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现在就有可行性(注:参见《中西部地方干部如何看待知识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即出。)。
附图
图2.教育追赶进程与经济追赶进程的比较
注:图中数据点为美国追赶英国、日本追赶美国以及韩国追赶欧洲(以法国为代表)过程当中,不同时期追赶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先行国的比例(纵坐标)与追赶国人均GDP相当于先行国的比例(横坐标)的比较。图中虚线为对角线,表示教育追赶进程与经济追赶进程完全一致的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麦迪森(1996)数据计算。
三、中国知识发展战略的实施:建立良治,优先实现基本知识服务的均等化
进入21世纪,知识资源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优势资源;反之,知识发展水平落后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运用知识促进发展,建立知识社会将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
如何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呢?我们认为,这首先要求政府转型,由“统治”(government)转向“治理”(governance)。治理的目标是良治(good governance,也译作善治),其核心是政府与公民有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良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质特征就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注: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研究发现,中国内部各个地区的政府管理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在这方面进行了定量化的研究工作。根据他们建立的政府效率指数,1996年全国政府效率排名倒数后8位中有7个是西部省区。西部11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和广西,不含重庆)中西藏政府效率指数最低(9.8),仅相当于政府效率指数最高的上海(84.4)的12%,西部最高的是四川(60.2),也只相当于上海的71%。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而知识发展对于政府转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知识与全球化的结合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其中,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知识对企业运行方式的影响已经得到重视,而知识对于社会运行方式,特别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在国内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上已述及,知识已经成为发展的主要源泉。正因为如此,知识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对象,而知识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性质又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Granham Leicester以编码和传播为维度(注:所谓非编码知识是指难以用语言、文字或者符号完整地表达的知识,又称为隐含知识。这类知识很难用简单的物理手段进行传播和复制,要掌握这类知识必须投身于相关的实践活动中,在实践过程中体会、理解和积累。而编码知识则是能够用语言、文字和符号完整地表达的知识,也成为显性知识。这类知识可以通过物理手段加以存贮和传播。),将知识分为四类,即未传播的编码知识、未传播的非编码知识、已传播的编码知识和已传播的非编码知识,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意味着不同的管理方式。适应于管理未传播的编码类型知识的官僚机构,已经不能胜任后面三种类型的知识的管理了,它们对应的有效的管理体制分别为个性领导、市场调节和团体共识(注:参见http://www. scottishpolicynet. org. uk。)。与此同时,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中,政府常常不能掌握决策所必须的全部信息,或者在信息的快速变化中显得呆板、迟缓。另一方面,知识发展增强了公民个人的知识能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良治起因于知识迅速发展造成社会系统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以及知识发展增强公民个人能力带来的公民社会发展;解决于知识发展引起公民和政府能力的增强,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成本的降低。
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基本国情,中国在知识发展战略的实施上应当分三个层次进行: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均等化的基本知识服务;二是加快促进知识的普遍应用;三是逐步增强知识创新能力。其中,前两个方面的能力为基本知识能力,而第一方面则是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的基础,应当作为优先的战略措施。
知识服务包括:促进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以及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激励机制和制度;能够造就具备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掌握现代技能的人口的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能够推动信息高效传播和处理的、充满活力的信息基础设施(注:参见前揭Carl Dahlman和Jean-Eric Aubert文)。其中,使公民在知识社会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服务,成为基本知识服务。基本知识服务均等化,就是保障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口在获得基本知识服务上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获得参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机会,避免被边缘化。
政府在实现基本知识服务均等化当中应当起基础性作用。首先,政府应当确定基本知识服务标准;其次,政府在保障基本知识服务均等化当中应当发挥促进者和监管者的作用;第三,在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本知识服务方面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还要作为提供者。
在制度供应方面,应当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和控制腐败定位为基本的制度服务。
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应当把普及12年教育和保障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机会作为基本的教育服务。在学校教育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在21世纪,能够获得改善生存状态的基本教育年限应当是12年,9年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改善生活的需要(注:例如,Robert Barro最近分析了100个国家1965年到1995年的数据,发现增长与以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很好的正相关性。Barro 认为这是由于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吸收先进技术,而中等和高等教育在这一方面尤为重要。参见Barro, Robert J.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vol. 91(2), 2001, pp.12-17.)。当前,国家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因此,中国应当把12年教育确立为新的国家教育目标,并构建相应的制度。
另外,建立覆盖全部人口的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也是基本知识服务的组成部分。使所有公民能够利用基本的知识基础设施、享受基本的知识服务,使中国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从而变沉重的人口包袱为巨大的发展资源,解决中国长远未来发展中的人口制约因素。
在信息基础设施及服务方面,应当把实现普遍接入作为基本的信息服务(注:作为一个与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相区别的概念,普遍接入(universal access)是指在合理的距离范围内有获得电信服务的公共途径,而普遍服务则是指电信线路接入到每个家庭。参见JohanErnberg, Universal Access for Rural Development fromAction to Strategies.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uralTelecommunications. Washington, 30 November-2 December, 1998。)。应当把建立覆盖全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普遍接入作为基本的信息服务内容,通过这种公共的接入途径,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农村人口、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边远地区人口获得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信息、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服务,从而防止边缘化。
【作者简介】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熊义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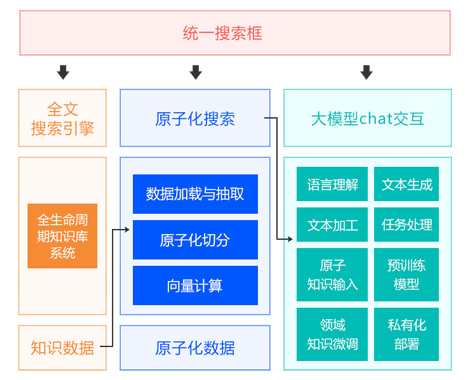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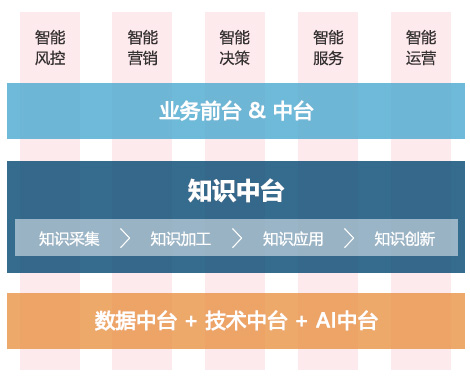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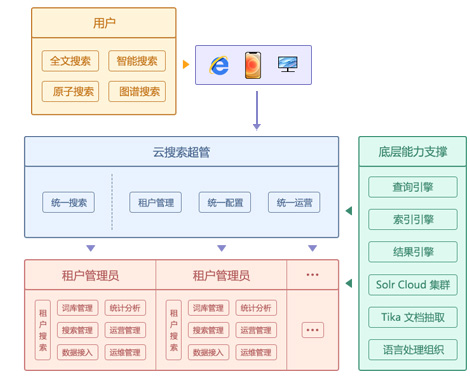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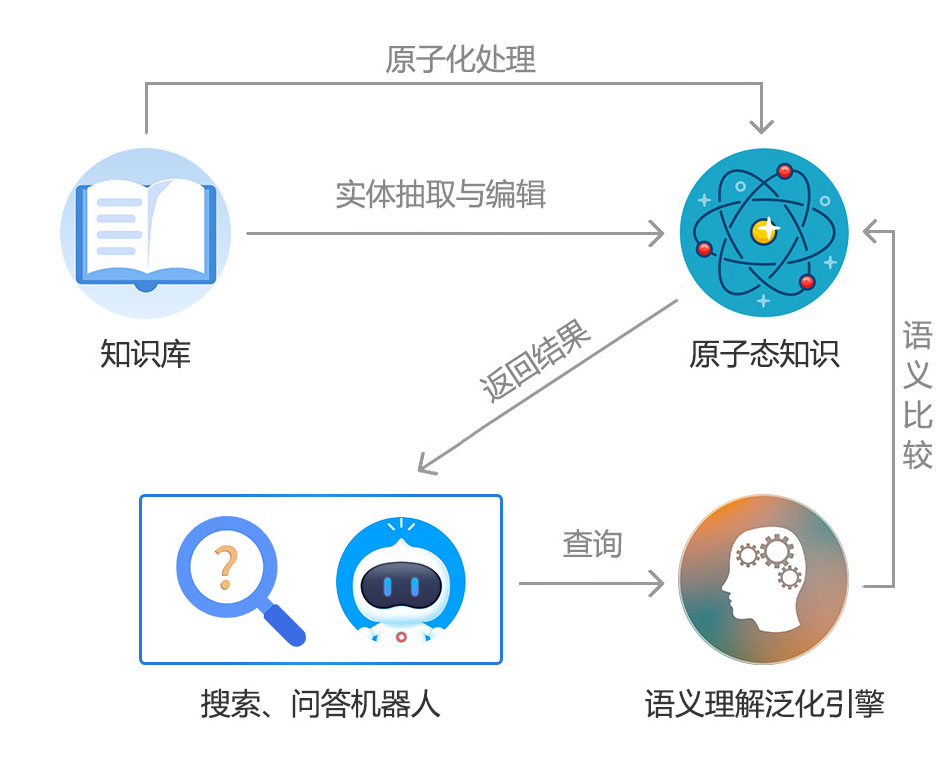
 2007-10-23 23:03
2007-10-23 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