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经济学性质
汪丁丁
林语堂不像老制度学家凡伯伦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来说明闲暇的重要性,他只写了一
篇散文“论谈话”,说的和凡伯伦几乎一样的事情,却更贴近我这篇短文的主题。林氏为
文,常常冷不防掷出一句话让你觉得妙不可言。譬如他在《论谈话》里谈到:“当我们看
见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耗费精力于无益的社交集会或当前政治论文撰作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关在监牢里
”。(《林语堂文选》下卷,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个人的闲暇多么有限和宝贵,他必须在成为文学天才、社交明星和政治撰稿人这三者当中作出决断的选择,我在《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八月)中已经解释了经济学始终没有明着解释给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分工原本是要给每个人更多的闲暇,结果每个人都越来越忙越来越受分工的奴役。我的解释基于三个基本的事实:(1)人类知识的各个部分之间有一种“互补性”,使得两项知识加在一起的价值可以大于这两项知识各自价值之和。(2)分工能够加快知识积累的速度。(3)分工使得没有人能够知道全部已经知道的知识。这三个基本事实加上假设不变的偏好或口味,就可以推出“每个人越来越忙”的结论。显然,要改变这个结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人们的口味,因为取消分工对任何人来说代价都太高了。而知识的互补性是知识的不可变更的特征,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足可以写几十篇博士论文了。改变口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日本的<SPS=0202>屋太一写了一本《知识价值革命》(三联书店中译本)前半部分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改变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习惯或以物质追求为基础的价值标准。
文学天才、社交明星、政治撰稿人,三者无非需要不同结构的知识而已(“创造性”与知识的关系要比这里说的知识经济学复杂的多)。若非如此,林语堂的那个办法也就不必要了。以有限的闲暇时间获取许多不同的知识,使得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产生最大的价值,这就是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的定义。把这个定义里边的关键词展开来解释,就是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关键词就是“知识”本身。其次是“知识结构”,也就是探讨知识的“互补性”。最后是知识的“价值”或探讨知识价值的产生过程。这是表述的顺序。理解的顺序往往正相反,最开始出现的概念最复杂。例如数学中“零”的概念,物理学中“物质”的概念,经济学中“成本”概念,心理学中的“心”,哲学中“概念”的概念,语义学中“意义”的意义,……推至极端,所有的信息传递似乎都有这个现象。复制生物所需的信息包含在种子或胚胎里。谁知道全部宇宙的信息是不是早就包含在“大爆炸”的那一点里呢?我理解,波普晚年提出做为“适应”(adaptation)的知识,就是在这个“信息”意义上理解知识的。(Karl
Popper,A World of Propensities,Thoem-mes Antiquarian Books
Ltd,1990)就我所知这是最宽泛的知识定义。因为任何带有结构的东西,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载着某种信息,关于“结构”的信息。所以波普提出过“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和“无意识的知识”(unconscious knowledge),后者包括遗传性习得的知识。
他又强调各种生物感官和器官获得和储存知识的能力,他指的是感觉器官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那些特定结构的获取和储存知识的能力。(Karl Popper and John
Eccels,The Self andIts Brai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作为“信息”的知识固然宽泛,却不很恰当。例如从外太空来的“3-k微波”明显地是一种结构或信息,但我们目前仍不能破译其涵义。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知识”呢?事实上,按照香农定义的“信息”概念,当一个观察主体面对着被观察的客体的最多的可能状态时,或者,一个接收到的信号包含最大的完全随机的噪声时,客体或信号所包含的信息也就最大。所以信息并不是“知识”,信息只是包含可能被知道的知识。当我们说我们拥有某项信息时,我们无非是在说我们已经提取出了那项信息所包含的知识。
另一个哲学家们喜欢用的知识定义是主观的知识,或者,用哲学家奎恩的话说:你认为你知道的东西就构成你的知识。(W.V.Quine,Pursuit of
Tru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主观知识的极端者应推麦克·博兰霓,他的名著《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i-chae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建基于他所谓“隐秘的知识”,从手工艺技巧开始,一切知识都是认知者主观参与和感情上认同的结果,都带有主观性。可是你认为你知道,你就“真”知道吗?这个问题就是奎恩那本书的主题——真理问题,也是他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分歧的所在,也叫“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或者,知识是否可以在一群人之间共享的问题(intersubjectivity)。于是知识问题又牵涉到语言或符号体系的意义问题。
不论如何,各家各派的知识定义于是总在“主观知识”和“无意识的知识”之间的什么地方。例如费希特、叔本华、胡塞尔、威廉·詹姆斯、哈耶克、罗素等等。我想我是不够资格给出我关于知识的定义的,上面这些话只是要为“知识”划出一块界域,好让我能继续说下去。
什么是知识的结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新的和老的认识论学者有相当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知识结构是按照逻辑推理的顺序从一个人所相信的最高层的假设依次向下排列的多层次假设的体系。例如当我们凭了每天的经验相信太阳从东边升起时,我们的思维逻辑自然地要求探索为什么如此。于是我们相信地球是从西向东自转,我们相信地球是球形的,我们相信在一定速度和距离内光线是“直线”,等等,总之,从这些更高一层的假设可以推出“太阳从东边升起”这一命题。然后我们会探求造成这些高一层次假设的原因或更高层次的假设。这样的逐层上推不仅使知识得以深入而且生出各自深入的专门知识。例如从我们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可以发展出几何光学和眼科学;从太阳发光引出化学和物理学;从旋转物质的球形引出宇宙学。每一科学存在的理由在于我们要检验与这一科学相关的层次上的那些假设。检验这些假设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相信(或更加不相信)这些假设。例如我们在上述那些科学的检验支持下就更加相信“太阳从东边升起”这一命题。但是这些检验又必须以更高层次的假设为基点。例如我们假设了“地球围绕太阳转”,而更高层次的假设必定涉及更多的其他专门科学以及它们的假设检验。每当新的事实否证了某一层次上某些假设时,我们必定试图修正该层次的其他假设和更高层次上的相关假设。结果不仅给其他学科里的假设也带来危机,而且我们不知道先修正哪一部分假设更好。波劳克在《当代知识论》里打了个比喻说知识论的全部想法就是研究怎样在大洋中间重建一艘大船。(John
Pol-lock,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Rowman &
Litt-lefield,1986)意思是在一个假设系统中先拆任何一部分都不行,必须同时调整全部的假设。这就是知识的“结构”。显然,知识的这种结构也就是知识各部分间的“互补性”。换句话说,知识的互补性产生于人类思维逻辑最基本的三段式和因果性联想。
知识的价值,像一切价值一样,只能是每个人的主观价值,也就是说只能以某人某时某地某状态下的偏好或口味来衡量某项知识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所包含的“净幸福”还取决于这人获取这项知识的成本。由于遗传性习得,我们的感觉器官获取知识的成本最小,而且由感官获得的知识总最有价值的。例如初生儿获得吃奶的知识,和他说的第一个单词——“妈妈”(由条件反射习得的知识),不可谓不重要。从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最大效用的那个中心渐次外推,知识的价值逐渐下降或者成本逐渐上升。于是这个人求取知识的动力渐次下降。原则上,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与上面说的全部知识的逻辑结构显然不是(或极少)重合的,因为一个人的效用受到他的社会分工的极大影响从而他的知识结构取决于他的分工。通常我们不会指望一个原子物理系大学生有兴趣学习开出租车,除非他所学的专业和将来由此而来的分工带给他的净幸福,与出租车司机相比微不足道。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闲暇时间(定义为维持生命所需的那部分时间之外的时间)大多被用于积累工业知识,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那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上,关于大规模生产的那部分知识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净幸福。大规模生产是怎样实现的呢?说到底是通过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实现的。越来越细的分工使一个人的闲暇时间能够专门用于越来越窄的工作(即在越来越窄的范围内求取技术知识)。而所有人的这种专业化过程降低了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所有人的购买力。所有产品的市场规模因此而不断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这个过程同时也就要求每个人效用函数的中心从而他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偏离全部知识的逻辑结构。因此人们知道得越来越多的同时,知道得越来越少。个人的知识结构越来越不同,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如果人们停止找寻关于互相合作的知识(即“制度知识”),那么工业化过程将是一个不稳定的、迟早会崩溃的过程,就像桥梁共振迟早要摧毁整座大桥一样。
碰巧读到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日,报道日本人如何利用“隐秘的知识”,引来与读者诸君共享。日本一桥大学两位研究人员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企业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他们说,本田汽车在八十年代决定推出崭新的车型时,只是靠了非常不明确的、隐秘的知识。其他汽车制造企业如尼桑也有类似的经验。日本企业利用隐秘的知识的办法,就是让雇员尽量在企业内部流动,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直觉。所以日本企业流行所谓“项目组合”,也就是以特定项目为中心临时抽调雇员组成的生产单位。
随着关于大规模生产的知识日积月累,随着人类生活口味的细致化和人际关系的文明化(即制度知识的积累),关于小规模多品种高质量生产的那部分知识的价值会逐渐提高。这也就是所谓“灵活生产方式”(或“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社会的特征是人们靠不断更新知识(而不是靠大规模生产)来改善生存条件。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物质方面的,就是所谓“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精神方面的,就是所谓“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有些误导的词,实际上是由于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非生产性资源运用,例如个人的全面发展,宗教的,文化的,等等)。于是技术性知识的重要性就被制度知识所取代。物质消费的发展将会停滞,但精神世界的发展将会加速。事实上,除非人类发现新的地球和新的生产方式,目前人口老化和生育率逐渐下降到自然更替水平的趋势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物质消费停止发展是必然的结局。技术知识对人类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还可以从技术进步的大趋势看出来。目前随着劳动工资增长和灵活生产方式的推广而正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技术和多功能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化,早晚会在大部分工业加工和组装领域取代人力。更进一步,自动编程的工作母机会取代人脑劳动中重复性强的部分。再进一步,至少熟悉数学的人能够想象,创造性工作中那部分目标可以确定,路径有待搜索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人或计算机工作母机去完成,这个前景的初级阶段就是现在发展的所谓“人机系统”——专家帮助机器人确定行动目标,机器人找出各种行动计划并搜索执行其中最好的。
总之,人类劳动会越来越偏重于创造性强的工作,而开发我们头脑的创造性,必然要求我们挣脱分工的局限,拓广我们大脑的知识范围和结构。这些相当于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更广的活动空间。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长期从事数学命题的计算机证明。计算机当然不能离开专家的直觉指导,但是计算机可以使专家免去细节的、琐碎的和重复性的证明工作,从那样的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用托玛斯·库恩的科学进步理论来说就是由专家给计算机指出各种可能的研究纲领,由计算机去完成每一个研究纲领在逻辑上要求的那些细节并且报告出结果。到那时候,科学家也许仅仅做为“方案科学家”而存在。
谈的很多都是梦想。我必须承认我胆子很大,居然企图在这么一篇文章里说清楚知识的经济学问题。“侃煽”之余,且自饮苏格拉底式解毒剂一服:“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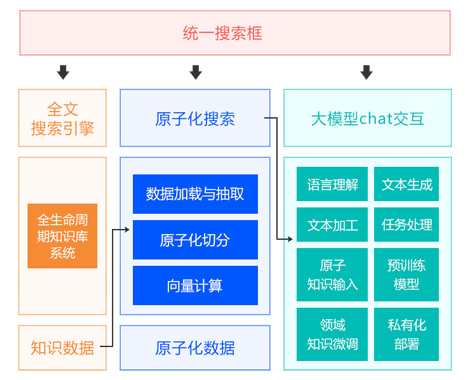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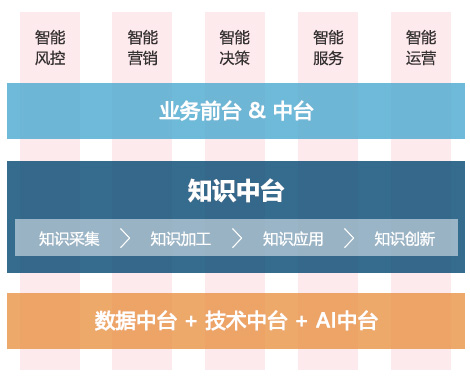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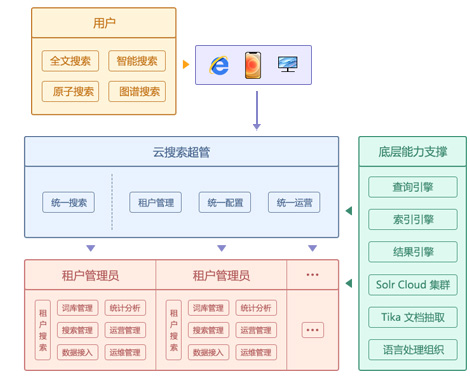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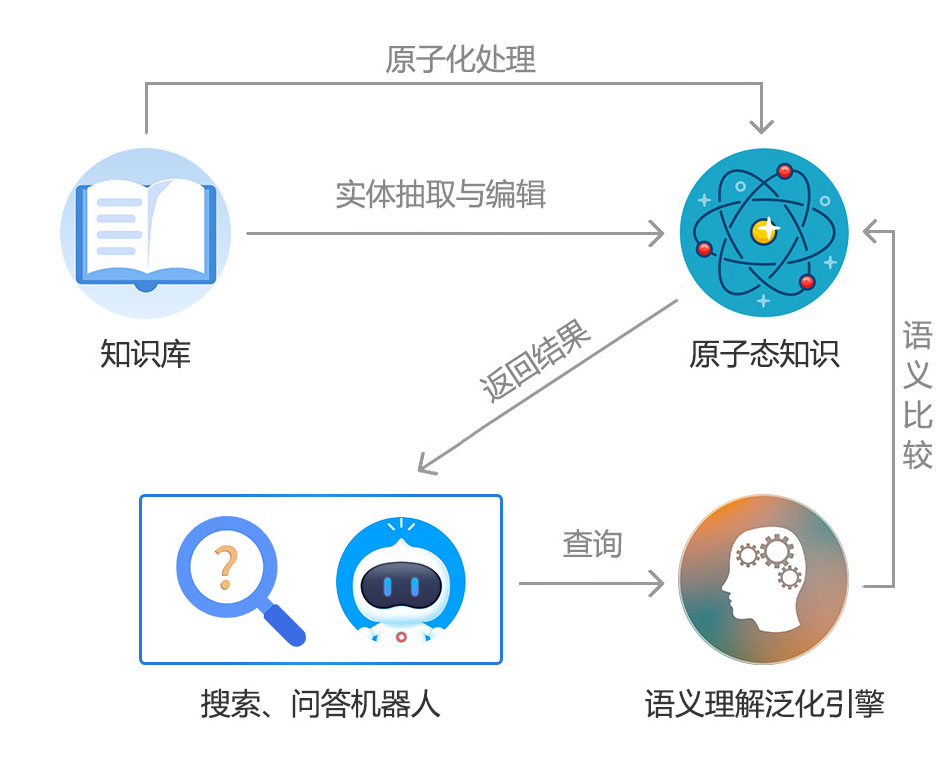
 2002-01-09 10:23
2002-01-09 10:23